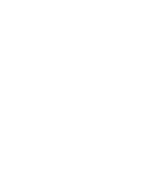根管手术做了四分之三,神经已经杀光了,就剩下要按照已经发往工厂的牙模做出来的嵌体。我的磨牙就留着一个大洞在那里,晚上和表弟吃烧烤,竟往里面塞了颗玉米。骑车送表弟去找美女富婆的路上,我时不时用舌头试图把它撩出来,像是在玩弄谁那顽皮的 G 点,直到差点翻车我才作罢。
到了地方,我们在寒风中等了快二十分钟,烟抽了一支又一支,活像两根烟囱。在我快要冻成棍子之前,表弟把烟一丢,踩了两脚,犹豫再三,尴尬地说:表哥,我成小丑了。
富婆和他聊了半天,最后给他说她跑去朋友家睡了。我服了,等不等都是次要的,我怎么就没有那种来我家借宿的美女富婆朋友?我看向表弟,他眼睛湿润了,不知是给天气冻的还是给富婆弄的。
我叹了口气:回哥谭吧,蝙蝠侠说他不打你了。
我有点没来由地生气,虽然不知道为什么,但肯定不是因为表弟带着我吹冷风。他陷在单身、楼凤和足浴城里太久了,我不想就这样放弃这个表弟。来之前其实他嫌远,是我一直在给他鼓励,鼓励到最后他愤愤地说了一句:妈的,去,大不了年底和富婆扯证。然后就坐上了我的车。那一刻他好似《逃学威龙》里的重案组之虎曹达华,差一点就要把软饭硬吃写在脸上了。结果软饭没吃到,西北风倒是喝了个饱。
我和表弟很像,我们都需要女人来拯救。我和表弟也不是特别像,他只需要操逼,而我像是陷在了泥潭中。生活像个冤魂一直把我往下拉,我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。而阿婷就像一个天使一样降临在我面前,把我从芸芸众生中拯救出来。
有时候我觉得我配不上阿婷:天使是有翅膀的,天使是会飞翔的,万一哪天天使厌倦了,展开翅膀飞走了,我要怎么办呢,我只能跑着、跳着、眼看着对方越飞越远,远成一个点,远到看不见,就像喜羊羊里每集都被打飞的灰太狼一样,可是灰太狼每集都会回来,但天使不会。
小时候大人们揍我时总是说:你翅膀硬了。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句讽刺的话。直到后来我发现我压根没有翅膀,大人们也没有翅膀,我才知道那是大人们的期盼,期盼我飞得高高的,永远不要回到泥潭里来。可我现在只有一辆电动车。我又想起了电动车的花语:我的电动车只能开五十公里,所以不要离我太远。